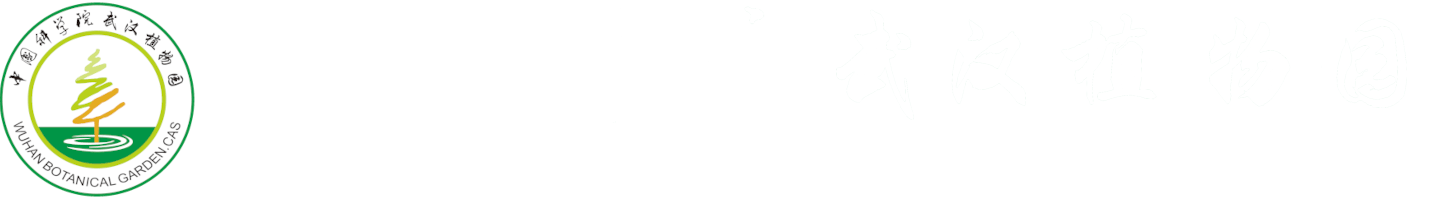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这是又一次出发,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胡光万研究团队正在规划4月的行程:去马达加斯加对一些特殊植物类群开展科学考察,“这时候恰好是旱季和雨季交替的时间,刚好可以考察这一时期特殊植物的形态”。
在植物分类学学者眼里,每一种植物都是独立个体,它们不仅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甚至“有性格、有心情”。
胡光万本人已经去过非洲三十多次,2007年至今,胡光万团队已发现52个新的植物品种,包括49个植物新种和3个新变种。源自非洲的发现共有16个,团队在领域内已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这体现着我们科研能力的提高,中国科学家也能走出去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研究”。
世界的广阔与浩瀚,通过植物亦可见一斑。在世界中寻找那些静默生长且不为人知的植物,是这群学者感知世界的方式。
在武陵山区发现植物新种
今年2月,胡光万研究团队在国际植物学期刊《BotanicalStudies》上发表新物种——在鄂西南武陵山区坪坝营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武陵腹水草。它既是该研究团队首次发现并命名的腹水草属植物,也是中国大陆近40年来所发表的该属植物的唯一新种。
新植物拥有姓名的流程讲究严谨,一般来说,运用专业手段鉴定新物种并给予规范特征描述的学者,可在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对新物种进行命名。
据《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等记录显示,目前我国约有3万多种高等植物,其中特有植物种类约1.7万余种,半数以上由西方学者命名。
“我们的植物分类学研究较西方晚了近两百年。”胡光万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张彩飞博士说,以我国的特有植物银杏为例,它在1753年被命名了拉丁名Ginkgobiloba,而国内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
“起步稍晚,但加速度大。”胡光万补充,从比对标本到野外调研,从精细解剖到分子研究,研究手段的升级让如今我国植物研究得以“放眼世界”。
胡光万是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骨干学术带头人,团队发现的16个植物新种及新变种来自非洲。让“长在深山人未识”的植物重见天日,从此有了姓名,让植物分类学学者收获成就感。
野外被毒虫叮咬是“家常便饭”
发表武陵腹水草的论文第一作者丁世雄是“95后”在读博士生,出生成长在江西赣州农村,他对于生态自然研究有浓厚兴趣。
一年365天,他们往往有一半时间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考察、辨识植物,每天平均下来步行超过十公里以上。从隔着印度洋的非洲到云南、西藏、四川,胡光万粗略统计,自己穿坏了十多双登山鞋。
前往非洲进行调查时,团队不仅要请来当地向导,有时甚至要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请求派来士兵进行人身安全保护。
一次野外科考中,8声枪响在前方不远处的树林中炸开。当时队伍里共有8人,事后,当地人解释:“8声枪响代表警告他们不要前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这次科考,团队发现一种珍贵的兰科植物,鉴定完成后,他们命名其为丹尼尔多穗兰,纪念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攻读博士学位却因病离世的肯尼亚兰科植物研究专家丹尼尔。
野外面临的困难超出普通人想象,擦伤、毒虫叮咬是“家常便饭”。胡光万说,在对准植物拍摄时,即便是感觉到蚂蟥已经叮在脸上,也必须咬牙忍受。他把裤腿卷起来,记者看到,两条腿上布满深浅不一的上百处疤痕,团队成员张彩飞也被蚂蟥咬过,他说,被咬时不算太疼,结痂后的痒才是钻心难耐,持续一周才会缓解。
出门旅游不看风景只看植物
家人曾抱怨,和胡光万出去旅游,他是不看风景的,只注意着路边的各种植物,兴致来了还喜欢给家里人讲课,头头是道。
从发现植物新种到最终发表,时间长短从几个月到超过10年都有可能。为了确认2006年10月第一次在贵州发现的泡萼凤仙花,胡光万四处查阅标本文献,要和所有已知凤仙花种类进行比较,再找到相关领域专家反复交流确认,最终得以命名,前后花费了15年时间。他们认为这种漫长“很浪漫,也有重大的意义”。
新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多地用在这一古老学科上。除了经典植物分类学的理论知识,他们同样使用分子系统发育理论和DNA测序技术来追溯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胡光万告诉长江日报记者,通过基因分析可画出“分子树”,也就是植物的“族谱”,能显示植物间的亲疏远近。
“择一事,终一生。”胡光万说,“当其他学科在追热点的时候,我们在积累;当其他学科在赶往新鲜点的时候,我们还在积累。”植物分类学研究者要像大树那样紧紧向下扎根汲取养分,才能屹立不倒,枝繁叶茂。
近年来,湖北接连发现新物种,仅今年开年就有3个植物新物种现身,这对于生态保护和生物进化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证明省内生态系统稳定、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保护成效显著。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刘克取 通讯员江珊)